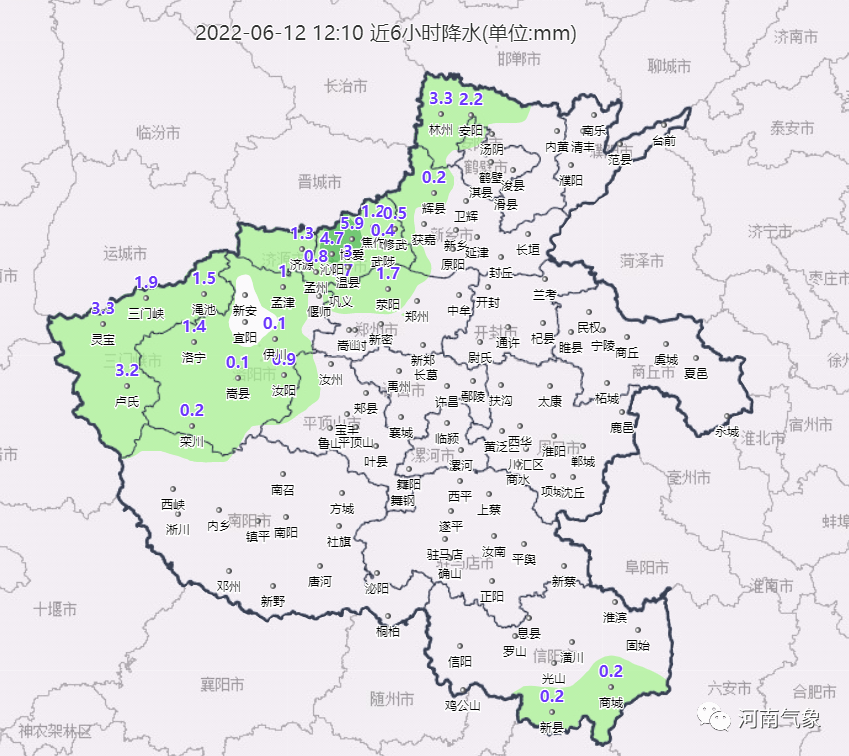一部“说出来”的小说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小说家有诉说一切的权利。无畏的小说家可以穷尽手段,写出任何不像小说的小说。就此而言,逄春阶的《芝镇说》似乎冲破了传统小说的窠臼,堪称一部小说之外的小说。
《芝镇说》本身就是“现代”的产物,它以连载的方式在报纸和网络平台同步推出,读者的即时互动或多或少会影响作品的叙事,使之成为一种时刻与受众连线的“云创作”。正是这种开放的“云同步”的写作方式,把《芝镇说》变成一部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小说:它面朝故乡,立足于芝镇,广纳家国传奇、时议流言,杂取种种“说”合为一说,欲说还休,自圆其说。故而,《芝镇说》的开放式写作使其具备了一种“著‘说’立书”的文体形式——它当然是逄春阶写出来的作品,但从文本上看,更像一部“说”出来的话本。在这里,小说家化身为说书人。小说的结构尽管近乎散漫,但是说书人的三寸不烂之舌总能将其说得端绪分明、头头是道,既说得开,又收得回,一切尽在“芝镇”中。
芝镇,脱胎于作者的家乡景芝镇。这里盛产美酒,乡人皆好酒擅饮,故常因喝酒留佳话,亦因喝酒闹笑话。所谓“芝镇狗四两酒”“芝镇猪,排山倒海酒呼噜”,芝镇的万物生灵似乎也有酒意。没有酒,恐怕也就没有了芝镇;没有酒香,也就没有了芝镇人一身的胆气和神魂。本书作者和小说的叙述者公冶德鸿也不例外,当属芝酒的传人。于是,《芝镇说》即如济南道人袖中的酒壶,虽只一壶,却是饮之不尽的“家传良酝”。作为说书人的逄春阶借人物之口,将一部小说写成了“大话”,把上百年的家事国事酿成了絮叨不尽的百转千回。《芝镇说》借酒说话,借酒话说出不可说不忍说不易说之话,所以这部书并非饮酒作乐借酒消愁,而是借酒疗病借酒去病——诊疗一个家庭乃至人世间“没有疤的内伤”。故而,与酒相对的另一重要线索便是药。《芝镇说》有如经年累积的医案卷宗,记录了芝镇人的集体症候,更记录了公冶家族及其乡里乡亲的个人行状,试图“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”。作为记者的公冶德鸿充当了主诉一切的代言人,由他穿针引线、内引外联,和盘托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和不知道的一切。这位记者不仅可以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作者更让他具备了“听懂一切”的特异功能:既听得上达天听的高头讲章,也听得不上台面的土话、瞎话,甚至鸟语、鬼话。所以这部书的主诉人表面上是记者公冶德鸿,实际还有醉话连篇的公冶令枢、公冶家族的不死鸟弗尼思以及“我亲老嫲嫲”(曾祖母)、“我爷爷”的亡灵。谁会拿醉话当真?又有谁能听取鸟语、鬼话呢?但是“诉说一切”的小说家可以“听见一切”,让那些从无机会面世的寂静之声化作倾动人心的神启之声。
最后来说公冶祠堂供奉的神鸟弗尼思。它就像无所不知的万事通,公冶一族的家史逸事,世间的名物掌故,一概张口就来;它还像深谙世道人情的老祖宗,不时臧否人物,令人醍醐灌顶。此鸟非凡鸟,是小说中的智者、精灵。谁能像它一般心口如一、了无挂碍呢?传说东夷部落的伏羲氏、女娲氏皆以风为姓,风通凤,风姓即凤姓,所以东夷尊崇凤鸟,以凤为图腾。根据词源,弗尼思(phoenix)来自古拉丁语。这样说来,供奉在公冶祠堂的弗尼思既是享本地香火的土鸟,又是一只中西合璧的不死之鸟。那么,它的“匪夷所思”确乎其来有自,它的“鸟语”当然可以超乎小说之上,成为比一切醉话、鬼话都要浩茫无边的神话。
维特根斯坦说,对于不可言说之物,我们应该保持沉默。《芝镇说》却说出了众多的“子不语”。孔夫子要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又要“敬神如神在”,关键问题不是神在不在,而是有没有敬畏之心。假如我们能够重返芝镇,或许也能饮酒以乐,诉说旷古的酩酊与澄明:同人于野,利涉大川。
(作者赵月斌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简传林继续领跑海南公开赛欧巡挑战赛次轮 肖博文单轮最佳冲至并列第三
北京时间10月14日,2023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巡挑战赛(以下简称海南公开赛)在儋州洋浦古盐田高尔夫俱乐部继续展开。首轮领先者、29岁深圳
2023-10-15当高尔夫遇见诗与海 2023海南公开赛欧巡挑战赛新闻发布会在儋州召开
北京时间10月11日,总奖金50万美金的2023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巡挑战赛(以下简称海南公开赛)新闻发布会在儋州召开,宣布赛事正式启动。新
2023-10-11白云山、融创乐园等景区9月9日恢复开放
9月9日,台风“海葵”残余环流已逐渐远离广州,影响渐趋减弱,市内各大
2023-09-09新锦动力半年报被问询:公司“高端装备制造”业务毛利率下滑、与2022年度变化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性?
9月8日晚间,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
2023-09-09同比增长52.6% 滴滴发布二季度业绩报告
[汽车之家资讯]9月9日,滴滴在其官网发布2023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,二季
2023-09-09微软发布Windows 11 Build 23541预览版更新,强调问题修复
【ITBEAR科技资讯】9月9日消息,微软今日发布了面向Dev频道的WindowsIn
2023-09-09
苏炳添、谢震业入围尤金世锦赛参赛资格 巩立姣冲击3连冠
2022-07-10
未来3个月 U21国足将与克罗地亚乙级队进行热身
2022-07-10
行走河南·读懂中国|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主场活动进行
2022-07-05